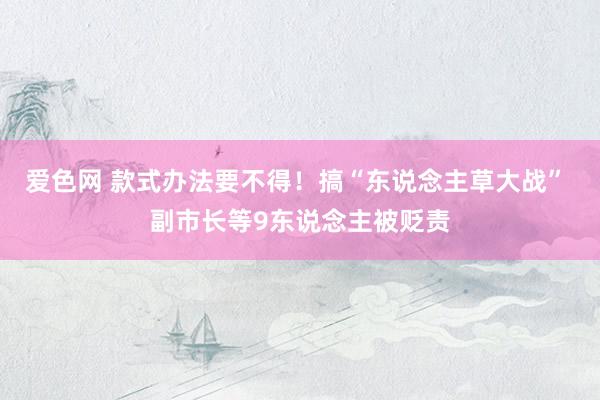玄色的使臣
人命里有这样重的敲击……我不知说念!
像神的歧视的敲击;彷佛因它们的压力
扫数诡秘的逆流都
停滞在你的灵魂里……我不知说念!
它们未几,但实在存在……它们在最严酷的
脸上留住裂痕,在最坚毅的背上。
它们许即是暴戾的匈奴王的小马;
或者死亡派来的玄色的使臣。
它们是你灵魂基督们深深的泻槽,
被庆幸亵渎的某个漂亮的信仰。
那些血腥的敲击是出炉时烫伤咱们的
面包的爆裂声。
而东说念主……哀怜的东说念主啊!他动弹着他的眼睛
当一个巴掌拍在肩膀上召唤咱们;
他动弹着他浪漫的眼睛,而扫数活过的东西
像一弯有罪的池塘停滞在他的瞥视中。
人命里有这样重的敲击……我不知说念!
同 志 爱
今天莫得东说念主来问我问题;
今世界午,莫得东说念主来向我问任何东西。
我一朵坟头的花也没看到,
在这样欢喜的光的行列里。
谅解我,天主;我死得何等少啊。
今世界午,每一个,每一个走过的东说念主
都不曾停驻来问我任何东西。
而我不知说念他们健忘了什么东西
空虚地留在我的手里,像什么生分的东西。
我跑到门外
对他们呐喊:
若是你们掉了什么东西,在这里啊!
因为在今生扫数的下昼里
我不知说念他们当着我的脸把什么门砰一声关上,
而某个生分的东西捏着我的灵魂。
今天莫得东说念主走过来:
而在今天,今世界午,我死得何等少啊。
残 酒
这个下昼雨异乎寻常地下着,而我
不肯意辞世,心啊。
这是一个暄和的下昼。不是吗?
被恩典与忧伤所装饰着,装饰如女东说念主。
这个下昼雨在利马下着,而我难忘
我的不义暴虐的穴洞;
我的冰块重压着她的罂粟,
比她的“你不成那样!”还要调皮!
我霸道、玄色的花;暴戾且
雄伟的石击;在咱们之间冰河般的距离。
她退得远远的默默将用毁灭的油
写下临了的句号。
那即是为什么这个下昼,异乎寻常地,我
隐忍着这只猫头鹰,隐忍着我的这颗心。
别的女东说念主走过我的身旁,看到我这样悲伤,
好心肠拿走一些些你
从我内心深忧歪绉的犁沟。
这个下昼雨下着,下得这样大;而我
不肯意辞世,心啊!
不朽的骰子
给Manuel Gonzalez Parda,因了这无羁而奇异的神志,众人他关怀地称赞我。
神啊,我为我的人命哀悼,
我后悔拿了你的面包,
但这块哀怜的想想的土壤
却不是在你腰间发酵的疥癣,
你可莫得逃脱的玛丽!
神啊,若是你当过东说念主的话,
你今天就会知说念该若何样作念神;
但你一向落魄不羁
绝不贯注你作念出来的东西。
而东说念主却得隐忍你:神是他啊!
今天我巫婆般的眼睛毁灭着
就像一个被判死刑的罪东说念主
是以神啊,你会点亮你全部的烛炬
而咱们将一王人来玩陈腐的骰子……
有可能,赌徒啊,当通盘寰宇
难免一死的庆幸输光了,
死亡的大眼睛会披露
如两只丧礼的泥么点。
而神啊,在这个暗澹、千里闷的夜晚
你能若何玩呢?地球已形成一个
因无标的的动弹而老早
磨圆的破骰子,
况兼无法罢部属来,除了在洞里
在谨慎的茔苑的洞里。
给我的哥哥迷古──丧祭他
哥哥,今天我坐在门边的板凳上,
在这里,咱们好想念你。
我难忘咱们常在这时辰玩耍,姆妈
总抚着咱们说:“不外,孩子们……”
此刻,我把我方藏起来,
一如以往,在这些薄暮的
工夫,但愿你找不到我。
穿过客厅,玄关,走廊。
然后你藏起来,而我找不到你。
哥哥,我难忘那游戏玩得让咱们
都哭了。
迷古,在一个八月的晚上
灯光刚亮,你藏起来了;
但你是悲伤,而不是欢叫盛兴地跑开。
而属于那些逝去的薄暮的你的
孪生的心,因为找不到你而不耐性了。而目下
暗影掉落进灵魂。
啊哥哥,不要让民众等得太久,
快出来啊,好吗?姆妈说不定在惦念了。
判 决
我出身的那一天
神恰好生病
每个东说念主都知说念我辞世,
知说念我是坏东西;而他们不知说念
那年一月里的十二月。
因为我出身的那一天
神恰好生病。
在我形而上的空中
有一个洞
莫得东说念主会察觉到:
以火光之花讲话的
放心的修说念院。
我出身的那一天
神恰好生病。
听着,昆玉,听着……
就这样。但不要叫我离去
而不带着十二月。
不丢掉一月。
因为我出身的那一天
神恰好生病。
每个东说念主都知说念我辞世,
知说念我嚼香烟……而他们不知说念
为什么在我的诗里柩车的
黑烟吱吱作响
焦燥的风──
自史芬克斯──沙漠中的探问者
身上张开。
每个东说念主都知说念……而他们不知说念
光患了痨病
而荫影臃肿……
况兼他们不知说念微妙会合成……
或者谁是那悲伤而声息好意思妙的
驼峰文轩 探花,自远方宣示
从边界到边界的子午圈的脚步。
我出身的那一天
神病得
很犀利。
○ 以上选自《玄色的使臣》
3、咱们的爸妈 (选自《Trilce》)
咱们的爸妈
他们几时会转头呢?
瞎眼的桑第雅哥钟正敲六下
况兼天仍是很黑了。
姆妈说他不会去久的。
阿桂提达文轩 探花,纳第瓦文轩 探花,迷古,
防备你们要去的方位,那处
迭影的鬼魂出没
当当弹响他们的顾虑走向
放心的天井,那处
母鸡仍惊魂不决,
她们吓得这样犀利呢。
最佳就留在这儿,
姆妈说她不会去久的。
不要再浮躁不安了。去望望
咱们的船。我的是最漂亮的了,
咱们成天玩的那几只,
不必争吵,事实是如斯:
它们仍然在池塘里,载着它们的
糖果,准备未来出航。
让咱们就这样等着,乖乖的,
别无选拔的,等
爸妈转头,等他们的补偿──
老是在门口,老是
把咱们留在家里
彷佛咱们不会
随着走开。
阿桂提达,纳第瓦,迷古?
我叫着,在昏黑中摸索我的路。
他们不成留住我一个东说念主,
我不可能是那独一的囚犯。
6、我未来穿的穿着
我未来穿的穿着
我的洗衣妇还莫得替我洗好:
一度她在她欧蒂莉亚的血脉里洗它,
在她心的喷泉里,而今天
我最佳不要想知说念 我是否让
我的穿着被不义的行为污秽。
如今既然莫得东说念主到水边去,
整刷羽毛的亚布遂僵硬于
我的刺绣样本,而扫数摆在夜桌上
原来会属于我的东西──
就在我的身边──
却不是我的了。
它们如故她的财产,
被她麦般的柔和安抚,情同昆季。
而只消让我知说念她会不会转头;
而只消让我知说念她会在哪一个未来走进来
递给我洗好的穿着,我心灵的
洗衣妇。在哪一个未来,她会舒畅性走进来
带着收尾,绽开笑貌,兴盛她
阐述我方实在知说念,实在约略
一付她为什么不成的容貌!
把扫数的絮叨弄蓝况兼烫平。
13、我猜度你的性
我猜度你的性。
我的心随着简便了。我猜度你的性,
在日间成型的婴儿之前。
我触到欢喜的花蕾,恰是绽放时节。
而一个陈腐的神志死了,
在脑子里腐化。
我猜度你的性,一个比荫影的子宫
更多产而动听的犁沟,
纵使死亡是由天主亲身授胎
分娩。
哦良心,
我猜度(是简直)开脱迟滞的野兽
它享受它想要的、能找到的一切。
哦,夕暮甜密的绯闻。
哦无声的喧闹。
闹喧的声无!
15、在咱们同睡过很多夜晚的
在咱们同睡过很多夜晚的
阿谁边缘,我目下坐下来等着
再走。故去的恋东说念主们的床
被拿开,或者另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往为别的事你会早早来到
而目下未见你出现。就在这个边缘
有整夜我依在你身边念书,
在你柔和的乳间,
读一篇都德的演义。这是咱们钟爱的
边缘。请不要记错。
我启动回忆那些失去的
夏令时光,你的来临,你的离去
眨眼间,知足,苍白地穿过那些房间。
在这个湿气的夜里,
如今离咱们两东说念主都远远地,我猛然跃起……
那是两扇开阖的门,
两扇在风中来来且归的门
暗影 对 暗影
18、哦小囚室的四面墙
哦小囚室的四面墙。
啊四面煞白的墙
涓滴无误地对着雷同一个数字。
神经的衍生地,暴虐的裂口。
你如安在你的四个边缘之间
扭拧你逐日上真金不怕火的看成。
带着大宗钥匙的慈蔼的监护东说念主啊,
若是你在这儿,若是你能知说念
到什么时辰这些墙还一直是四面就好了。
咱们就会合起来反抗它们,咱们两个,
遥远要多出两个。而你不会抽搭,
你会吗,我的救星!
哦小囚室的墙。
长的两面最叫我不幸,
彷佛两个故去的母亲,在昏黑中
各自牵着孩子的手
穿过虚幻的
下歪斜面。
而我零丁地留在这儿,
右手高高地搜寻着
第三只手,来
护养,在我的何处与何时之间,
这个无谓的成东说念主期。
69、你若何追猎咱们……
你若何追猎咱们,哦抖动着教条般
卷册的海啊。若何不幸亏雄伟啊
你在发热的日头的巢窟里。
你用你的手斧报复咱们,
你用你的刀刃报复咱们,
在浪漫的芝麻里乱砍、乱砍,
当波涛抽搭地翻身,在
漏下四方之风以及
扫数的大事纪录之后,千万只饰边弯曲的
钨的大浅盘,犬齿般的削弱,
以及狂喜龟类的L字。
随着日间的肩膀心虚的颤抖
震撼着的黑翼的玄学。
海,笃定的版块,
在它单一的书页上反面
对着正面。
77、雨雹下得这样大,彷佛我应该记起
雨雹下得这样大,彷佛我应该记起
况兼添加我从
每一个风暴喷口征集来的
珍珠。
这场雨千万不要干去。
除非如今我约略为她
落下,或者被下葬
深浸于自每一处火迸射
过来的水里。
这场雨会带给我若干东西呢?
我怕我还有一边腰干着;
我怕它会陡然罢手,留住我孤寂地
在不真正的声带的干旱里,
在那上面,
为了带来协和
你必须一直起飞,不成降下!
咱们不是往下升吗?
唱吧,雨啊,在仍然莫得海的岸上!
○ 以上选自《Trilce》
我 在 笑
一个小圆石,只一个,最下面的一个,
甘休了
整座预见凶险、法老似的沙丘。
大气有了顾虑与渴慕的垂死
而在阳光下静静地陨落
直到它向金字塔宝石要它们的颈子。
渴。流浪的部落水化物的忧郁,
一滴
接
一滴,
从世纪到分钟。
有三个平行的三,
留着太古髯毛的东说念主
行进着 3 3 3
这晓喻是伟大鞋店的期间,
是光脚行进的期间
从死亡 朝向 死亡。
九只怪物
而不幸地,
不幸通常刻刻在这个世界孕育着,
以每秒三特地钟的速率,一步一形态。
而不幸的实质是两次的不幸
而殉国的境况,食肉的、狼吞虎咽的,
是两次的不幸
而最白嫩的草地它的功用是两次的
不幸
而存在的平正,是双倍的加害咱们。
从来,东说念主类之东说念主啊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多不幸在胸间,在衣领,在钱包,
在玻璃杯,在宰杀摊,在算术里!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多不幸的神志,
远方从来不曾挟制得这样近,
火从来不曾如斯传神地上演它
死火的脚色!
从来,健康大臣啊,从来不曾见过
更致命的健康
不曾见过偏头痛从额头榨出这样多额头!
而居品在它的抽屉里装着的是,不幸,
心在它的抽屉里,不幸
蜥蝪在它的抽屉里,不幸。
困厄孕育着,昆玉啊,
比引擎还快,以十具引擎的速率,随着
鲁索的牲畜,随着咱们的面包;
暴虐不知说念为什么原因孕育扩张着
它是一场自生的急流
带着它我方的土壤、我方的固体云。
诡秘倒置位置,以一种
叫水质的幽默垂直赠给着的
函数,
眼睛被看到而这只耳朵,被听到,
而这只耳朵在放电的工夫敲了九下
丧钟,九阵讥刺
在麦的工夫,以及九声女音
在抽搭的工夫,以及九篇赞歌
在饥饿的工夫,以及九声轰隆
九声鞭响,减掉一声吶喊。
不幸捏着咱们,昆玉啊,
从背后,从侧面,
逼咱们浪漫摄入电影,
将咱们钉进留声机,
将咱们拔通达到床里,垂直地掉进
咱们的车票,咱们的信;
诡秘重且大,你不错祷告……
因为不幸的缘故
有一些东说念主
被生出,一些东说念主长大,一些东说念主故去,
而另有一些东说念主生出来但莫得死,另有一些东说念主
既不曾生也不曾死(这是最多的)。
况兼因为诡秘的
缘故,我从新到脚
充满哀伤
看到面包被钉死于十字架,萝卜
流着血,
洋葱抽搭,
谷类率皆成为面粉,
盐巴磨剩粉末,水逃开
酒成为戴荆冕的耶稣像,
雪如斯苍白,而阳光如斯被烧焦!
若何,东说念主类的昆玉啊,
若何能不告诉你我仍是无法再
我仍是无法再约略隐忍这样多的抽屉,
这样多的分钟,这样多的
蜥蝪以及这样多的
倒错,这样多的距离,这样饥渴的饥渴!
健康大臣啊:要若何办呢?
不幸地,东说念主类之东说念主,
昆玉啊,要办的东西太多了!
白石上的黑石
我将在豪雨中的巴黎故去,
那一天早仍是走进我的顾虑。
我将在巴黎故去──而我并不胆怯──
在某个跟今天一样的秋天的星期四。
一定是星期四,因为今天(星期四)当我提笔
写这些诗的时辰,我的手肘不安得
犀利,而从来从来,我不曾
嗅觉到像今天这样的颓靡。
西撒‧;;瓦烈赫他死了,每一个东说念主都狠狠地
锤他,诚然他什么也没作念。
他们用棍子重重地揍他,重重地
用绳子;他的证东说念主有
星期四,手肘骨
颓靡,雨,还有路……
强度与高度
我想要写,但出来的唯有泡沫,
我想要说很多东西,而我却堕入僵局;
每一个声息的数字都是一笔数量,
每一座笔墨的金字塔都得有个中枢。
我想要写,可是我只嗅觉到一只豹;
我想要用桂冠加冕,但它们却发着洋葱味。
每一个说出来的语字都与潸潸平等,
每一个神或神子的出现都得经过预言。
既然这样,让咱们去吧,去吃青草,
抽抽泣噎的肉,哀伤的果实
咱们腌存着的忧郁的灵魂。
去吧,去吧!我已受苦太多;
让咱们去喝那仍是探求过的,
让咱们,啊乌鸦,去叫你的爱东说念主怀胎。
饥饿者的刑轮
我发着臭气,穿出我方的牙缝,
吼怒,推动,
挤落了我的裤子……
我的胃空出,我的小肠空出,
阑珊把我从我方的牙缝间拖出,
我的袖口被一支牙签钩住。
谁有一块石头
不错让我目下坐上去?
即使是那块绊倒刚分娩过的女东说念主的石头,
羔羊的母亲,缘由,根源,
有莫得这样一块石头?
至少那另一块除去地
钻进我灵魂的石头!
至少
刺马钉,或者那坏掉的(虚心的海洋),
或者致使你不屑于用来丢东说念主的一块,
把它给我吧!
要否则那块在一场期侮中孤独且被戮刺的石头
把那块给我吧!
即使是歪曲、加冠了的一块,在那上面
正大良知的脚步只一度回响,
或者,若是莫得其它的石头,就给咱们那块以优好意思弧度抛出,
行将自动落下,
以贞洁的内脏自居的,
把它给我吧!
难说念莫得东说念主约略给我一块面包吗?
我将不再是一向的我了,
只求给我
一块石头坐下,
只求给我
(托福你们!)一块面包坐下,
只求给我
用西班牙语
某样终于不错喝,不错吃,不错活,不错休息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走开……
我发现到一个生分的形骸,我的衬衫
破烂而浑沌
我什么也莫得了,真可怕哪。
○ 以上选自《东说念主类的诗》
乞 丐 们
叫花子们为西班牙战役
在巴黎行乞,在罗马,在布拉格
并因此,过程伏乞、未开化的手,
鉴证了使徒们的脚,在伦敦,在纽约,在墨西哥。
他们参加了一份,向天主苦苦
条件圣丹德尔,
一场迄今无东说念主败过的竞赛。
他们把我方投献给陈腐的
诡秘,他们怒吼,对个体哭出
群体的子弹,
以呻吟报复,
以单纯的行乞杀敌。
一个步兵的祈求──
他们的兵器沿着金属进取祈求,
他的震怒祈求,比凶恶的炸药更能射中环节。
千里默的中队,他们以
致命的节拍放射他们的温驯
从门口,从他们自己,啊从他们自己。
潜在的战士,
将雷声的蹄铁钉上他们赤裸的脚跟,
暴虐的,数字的,
拖着他们习用的名字,
面包屑在臀部,
一枝双管的来复枪:血以及血。
诗东说念主向武装的诡秘请安!
注:圣丹德尔,西班牙北部之港城,隔邻曾发现史前期洞穴,上有壁画。
给一位共和军英豪的小祷告文
一册书长留在他故去的腰际,
一册书自他故去的躯壳萌芽。
他们带走了英豪,
而他历历如绘而不幸的嘴巴投入咱们的呼吸;
咱们汗如雨下,在咱们肚脐的重任之下;
流浪的月亮跟随咱们;
死者,雷同地,也因悲伤流汗。
而一册书,在托雷铎战场,
一册书,在其上,在其下,一册书自他的躯壳萌芽。
紫色的颊骨的诗集,在说与
未说之间,
用奉陪着他的心与说念德音信写成的
诗集。
书留住,其它什么也莫得,因为茔苑里
一只虫豸也莫得,
而沾血的空气留在他的袖边
逐渐虚化,没入不朽。
咱们汗如雨下,在咱们肚脐的重任之下,
死者,雷同地,也因悲伤流汗
而一册书,我感动地看到,
一册书,在其上,在其下
一册书霸道地自他的躯壳萌芽。
群 体
战事实现,
战役者故去,一个东说念主走上前
对他说:“不要死啊,我这样爱你!”
但故去的躯壳,唉,仍然故去。
另外两个东说念主走曩昔,他们也说:
“不要离开咱们!勇敢活过来啊!”
但故去的躯壳,唉,仍然故去。
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五十万个东说念主跑到他身旁,
呐喊:“这样多的爱,而莫得半点措施拼集死!”
但故去的躯壳,唉,仍然故去。
成百万的东说念主围绕在他身边,
众口一词的苦求:“留在这儿啊,昆玉!”
但故去的躯壳,唉,仍然故去。
然后全世界的东说念主
都围绕在他的身边,悲伤的尸体感动地看着他们:
他缓缓起身,
拥抱过第一个东说念主;启动往来……
西班牙,从我这儿把这个杯子拿去
世界的孩子们
若是西班牙垮了──我是说若是──
若是她从天上
垮了下来,让两张地上的岩床
像吊腕带一样收拢她的手臂;
孩子们,那些凹洼的寺院是若何样的年代啊!
在阳光中我传给你的音信何等早啊!
在你胸华夏始的吵声何等急速啊!
在熟谙本里你的数字2有何等陈腐啊!
世界的孩子们,姆妈西班牙
她穷困地挺着肚子;
她是手持藤条的咱们的憨厚,
是姆妈兼憨厚,
十字架兼木头,因为她给你高度,
晕眩,除法,加法,孩子们;
饶舌的父母们,是她在照看一切啊!
若是她垮了──我是说若是──若是西班牙
从地上垮了下来
他们将若何罢手长大,孩子们!
若何年事将处置它的月份!
若何牙齿将十颗十颗地串在一王人,
双元音化作念钢笔的笔划,堕泪的勋章!
若何年幼的羔羊它的腿
将接续被雄伟的墨池塘所绑着!
若何你们将走下字母的道路
到达悲伤所生自的字母!
孩子们,
斗士的子孙,暂时
压低你们的声息,因为此刻西班牙正在
动物的王国里分发人命力,
小花、流星,还有东说念主哪,
压低你们的声息,因为她深浸在
她伟大的强热里,不知说念该
作念些什么,而在她的手中
头颅在讲话,纷至踏来地说着说着,
头颅,有发辫的头颅!
头颅,充满活力的头颅!
压低你们的声息,我告诉你们:
静下你们的声息,音节的赞颂,事物的
抽搭以及金字塔隐微的谜语,啊致使静下
被两颗石头压着的你们太阳穴的呻吟!
压低你们的呼吸,况兼若是
她的手臂掉下来,
若是她的藤条咻咻地鞭打,若是夜已莅临,
若是太空在两片地狱的边缘地区间找到它的位置,
若是那些门的声息喧哗起来,
若是我来迟了,
若是你看不到任何东说念主,若是钝的铅笔
吓倒了你们,若是姆妈
西班牙垮了──我是说若是──
快出去,世界的孩子们,快出去找她啊……
○ 以上选自《西班牙,从我这儿把杯子拿去》
色吧